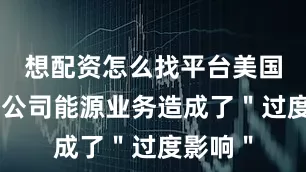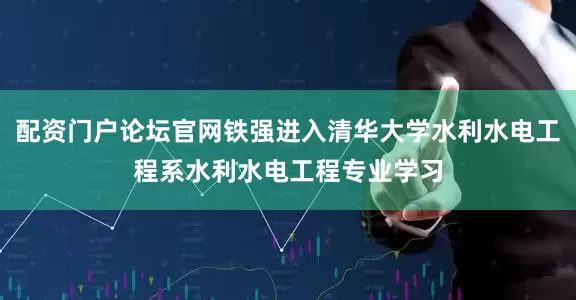1947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,西安城南的碉堡灯火闪烁。胡宗南身穿军大衣,站在地图前沉思,警卫员跑过来汇报:“行动处传来消息,查获电台时发现几份可疑名单。”胡宗南只抬头问了一句:“名单里有熊这个名字吗?”得到否认后,才挥手示意下属退下。那一瞬间,便决定了熊向晖此后命运的走向。
关于北平交道口电台被毁的消息,没几天就传到了西安。王石坚被抓,湛筱华住处被搜查,她的关系链也直指当时正在美国读书的熊向晖。保密局里面一时间情绪高涨,觉得大事即将水落石出。不过,京沪那边的加密电报反复传达了三天,胡宗南一直没有点头批准深入追查,搞得局里不少人都摸不着头脑。

不得不说,这位西北“要员”心里的顾虑并不复杂。熊向晖是他亲手挑选的秘书,就算他对蒋介石“政治可靠”这招牌的维护,也离不开他。写延安作战指令,要润色公文,甚至给蒋经国写信也总叫熊动笔。这种近身的信任,一旦被揭露是“伪装下的幌子”,他在军中的地位瞬间就会崩塌,自己费心经营的“嫡系”身份也会随风而逝。
有意思的是,最能体谅胡宗南处境的,偏偏是另一头的周恩来。这个人以冷静出名,他判断王石坚即使被审讯,也未必能真正查出熊向晖的全部身份。两个原因:一是王对熊的详细背景还不够了解,二是保密局和胡宗南那边关系复杂,各自为政,反而让信息变得模糊,互相过滤。果然如此。在西安整理案卷的时候,叶翔之发现资料中牵扯出胡系的人物,于是立马向毛人凤请示。毛人凤一句电话:“先报胡长官”,案件就被划出了一个“特别封存”的红线。

当时,沈醉正为几万包面粉卡在西安不敢动弹,烦得很。叶翔之拉着他到一边,小声问:“沈处长,胡长官脸色很难看,要不要硬碰,还是就装作不知道?”沈醉回忆中记得自己当时的答话:“先稳住,等南京那边指示。”结果南京也没打电话告诉他们具体要怎么做,紧接着胡宗南组织了一场宴席,把两位特务头子叫去喝酒。还没开始吃饭,胡就把叶叫到走廊上,说:“这几个人由我来安排,不要告诉他们。”一句话就把所有调查的事都封住了。
转到1948年春,熊向晖在克利夫兰寄出成绩单和论文题目,胡宗南拿到复印件时,亲笔批示:“留学优良,俟成归国效力。”那年秋天,解放军在陕西中部的战果频繁传来,好消息不断。国民党在西北的军心开始动摇,蒋介石下令胡宗南“死守关中”。胡宗南这才后悔无及:他手里最懂共军套路的人,竟然远在海峡那边,而且已经不再是自己真正的部下。可他依旧选择沉默不语,因为一旦说出真相,面对的责任可不止是被免职那么简单。
沈醉获特赦后,写了篇《我的特务生涯》,对当年在西安的事情只提了几句,但每一句都直指核心。他确认了毛人凤发电命令“材料先交胡宗南”,还记得胡在宴会中反复叮嘱:“老先生要是知道我身边有人潜伏多年,肯定会大发雷霆。”这一段的旁证,巧合地和周恩来后来对熊向晖的评价呼应——“胡宗南不是在保护谁,而是在自保”。

1949年7月,熊向晖回到国内,在北京饭店和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。周强调:戴笠去世后,保密局由多方共同管理,郑介民和毛人凤都要依靠胡宗南的力量来制衡军政部,他们也都希望维护自己的面子,所以选择了沉默不语。熊向晖问:“他们不怕我回国吗?”周摇了摇头:“他们倒是更担心你的身份一旦确定,老蒋会迁怒他们。”这个推理在后来川西战役中得到了验证。胡宗南三次请求南撤都未获批准,最终在西昌战败。蒋介石趁机发泄私怨,差点就把胡宗南留在大陆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,胡宗南还是搭上郭寄峤的顺风车才飞到台湾。郭回忆说,蒋介石那会儿的原话是“让他自裁也罢”。原因就不用多说了吧:延安失利、陕北连败,都跟情报泄漏有关系,而漏洞正好出在胡宗南的幕府。蒋介石对胡宗南不太相信,甚至都不愿再见面,这种冷淡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慢慢缓过来。

1991年,台湾《传记文学》连载《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》,一时间让岛内议论纷纷。张佛千写了篇文章,说:“原来毛对胡军的动向了如指掌。”他依旧试图把失败怪在特工渗透上,而非战略上的失误,但也在侧面承认了熊向晖的作用。到此,关于当年西安事件的真相才算是逐渐完整:熊向晖被揭露,但因为胡宗南和毛人凤合力封口,他得以全身而退;胡宗南“放他一马”,其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;毛人凤则顺势而为,也算是保住了自己情报系统的面子。
回到那晚的地图室,胡宗南没想到自己随意一个动作,最终让国民党西北战场彻底失去了翻盘的希望。沈醉的回忆让后人明白:打仗不仅仅是兵力比拼,更是一场情报和心理的拉锯战。熊向晖能平安回来,靠的不只是个人的忍耐,还得依靠对手的顾忌,而这种顾忌,实际上源自复杂的人性和派系之间的纠葛,跟仁慈没半毛钱关系。
京海配资-京海配资官网-专业实盘配资-比较正规杠杆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